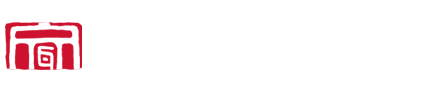2020年7月11日,《光明日报》“光明书话”栏目刊载了我院唐小林教授的新作《构筑一座“故乡博物馆”——读漠生的<又见炊烟>》,该文后被《中国环境报》全文转载。
《又见炊烟》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漠生先生的散文集,于今年3月正式出版发行。唐小林教授从面对故乡时“逃离而又渴望回归”的情感出发,解读了《又见炊烟》中的川中风情、乡音乡愁,以深情的笔触展现了漠生先生何以为当下的人们构筑了一座前现代的“故乡博物馆”。

《光明日报》2020年07月11日12版(右两栏为唐小林教授作品)
附:作品原文
构筑一座“故乡博物馆”
——读漠生的《又见炊烟》
背靠在故乡的老床上,我打开漠生的《又见炊烟》。子夜,下凉了,伏天变得温顺而体贴,渐渐消去了暑热的狂傲,这对于我的第三故乡而言,简直是一种梦想。而第一故乡,生我养我的远方,此时应是月明星稀,凉风扰扰,稀疏的几声犬吠,掠过祖先们芳草萋萋的坟头,在那片魂牵梦绕的土地上,写下寂寞与荒凉。这也许就是我与作者漠生面对故乡时共同的人生境遇:逃离而又渴望回归,回归又发现道路早已阻隔。我们被抛入一种不及物的中间状态,既不在彼岸,也不在此岸,而只能困在“第二故乡”,作一次又一次精神的“还乡”。只有儿时那一缕缕袅袅的炊烟,牵住我们漂泊的目光和脚步。我们是一群“丧家”的孩子,流浪在无依无靠的大地上,除了那点点滴滴挤满心房的乡愁。《又见炊烟》正是写出了这种困境、悖论与无奈,从而写出了整整一个时代一群人的生存状态。
川中的夏家沟竹林湾,这个特殊的地名,是故乡的代名词。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那批励志、考学、出走,多年以后跻身都市的游子,无不在心中不断“回望”这片叫作各种各样“竹林湾”的乡土。在我的经验范围内,他们大都没有“衣锦还乡”的喜悦与虚荣。当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坎坷打通“城市”与“乡村”、“繁华”与“落后”以后,在遥远的时空距离中,他们有了足够的审视“自我”“乡土”“中国”的位置与角度,他们变得特别宽厚、善良、悲悯与谦卑,打心底原谅了在那片土地上所经历的饥饿、贫穷与疾病,奚落、鄙视与凌辱,原谅了与“苦难”纠缠在一起的全部“摔爬滚打”。故乡的一草一木、一鸟一石,那山那水,那人那物,乃至遗闻轶事,在他们“想家”的婆娑泪光中,都变得如此深情、如此美好,作为精神底座,足以支撑他们的生命世界。美,光泽万物,《又见炊烟》在“失去故乡”的深层隐痛中,深刻地发现了故乡的美好,唤醒了关于故乡的良知,可谓用文字雕刻和塑造了一群人特殊的情感经验。如今,还有什么比用文字唤醒真情、良善和美更为珍贵?
在漠生的笔下,儿时故乡的天人合一,既是源于“自然”与“天然”,更是根源于赤子最初萌动的“良知”。换言之,《又见炊烟》以生动的笔触见证,天人合一不是某种自然天成,而是人的良知的一种发现,离开人的良知,天地离分,人神异域。一只斑鸠幼仔,被“我”和弟弟在竹林下的草窝里捡得,从此与“我们”的命运发生关联,“我们”像尊重和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呵护它。它成长,“我们”也成长;它飞翔,“我们”的情感也飞翔,并在它的飞翔中体会自由对于生命的奥秘;它信守,“我们”也学会信守;它总是在该飞回的时候飞回,“我们”也总是在它飞回的时候守望;它眷念,“我们”也懂得眷念;它总是在屋前屋后盘旋,亦如今天“我们”的内心期盼总是萦绕在故乡的屋檐。有一天,它飞走了,“我们”突然在伤心中明白了自由与独立对于一个生命是何等的重要。《那只飞走了的斑鸠》由此介入了我们的心灵:是良知沟通了陌生的生命,又是无数渺小微弱的生命,开启并丰盈了人类的良知。一旦我们在任何一个生命面前闭上眼睛,我们也就关上了良知的大门,同时我们也就关上了这个世界“美好”的最后一扇窗户。我从《养兔子》《大灰狗》等篇什中读出的几乎全是这样的东西。
不是苦难见真情,而是真情让我们共度苦难,也是真情在多年以后让我们感谢苦难。《夕阳西下时》,华哥悠扬的二胡演奏,已经超出音乐的意义,它是人们逃脱苦难念想的另一种高雅的表达。华哥才艺的高低,已经无足轻重,重要的是,他总是在人们需要精神安抚的时候出场,在那些个艰难时刻,心心相慰、惺惺相惜。这才是艺术的真谛。《苦难和幸福的妈妈》《小学王老师》《大天干年代的讨口子》《高中班主任陈老师》《师兄光学》《少年病事》等篇,讲述了各色故事,描绘了不同的人物,但都在或是血缘之亲、或是师生之情、或是同窗之谊、或是萍水相逢中,表达了“真情”。《又见炊烟》跳出苦难写真情,篇篇写得情真意切,动人肺腑。作者漠生,无疑是一个多情、记情、念情、深情的作家,更是一个知恩、懂恩、感恩、报恩的写作者。我猜测,过了“知天命”之年,他还要殚精竭虑地用文字记下故乡的那些琐屑的物事,不仅是要雕刻那些生命的时光,更是要留住那些包含了人类童年永恒情愫的记忆,为飞速“现代化”途中的人们,构筑一座苦难与真情彼此相依的前现代的“故乡博物馆”。这或许既是他的“知天命”,也是他的“天命”?
是的,《又见炊烟》是一座小小的“前现代”的“故乡博物馆”。它首先是故乡的风物志。《磨出来的美味》中的“石磨”,是前现代中国乡村的标志性器物,它磨碎的不仅是五谷杂粮,磨出的也不只是麦面豆花,而是古老中国乡村社会的艰辛、智慧与不屈的生命韧性。《又见炊烟》也是故乡的地理志。《蛮洞子》《我的琼江河》《公社城堡》《潼南的崇龛场》等,全都是靠记忆描摹的前现代时期的“文学地理”。有的诡异而神秘,像“蛮洞子”;有的充满无端的恐惧,犹如一个孩子面对深不见底、一生也走不出的迷宫、城堡时内心的战栗。而琼江河就是一位乳汁丰沛的母亲,“琼江”即是“琼浆”啊,在“我”的生命中涓涓流淌,永不干涸。“崇龛场”则是“我”儿时的《清明上河图》,那里有我的欢喜,有我因为生活困苦而曾经羞于启齿的往事。《又见炊烟》更是乡土中国的风俗志。《为大姐送亲》《大年初一看杂技》《清红苕》《儿时捕鱼记》《回老家烧纸》《乡村娃娃看电影》《赶鸭人》《自留地里的美食》等,记下了川中的各种仪式、习俗与特定时代人们的生活情状、生命形式和精神样态。
《爷爷,你在哪里》,特别具有深意:寻祖、寻根,寻觅生命的来龙去脉,寻找人类的意义源头,或许正是《又见炊烟》的命意。可是,爷爷你在哪里?
炊烟,一旦从故乡升起,就将永不飘散,它牵动的是人类永恒的乡思。
(来源:《光明日报》2020年07月11日 12版)
编辑/王北辰
责编/操慧